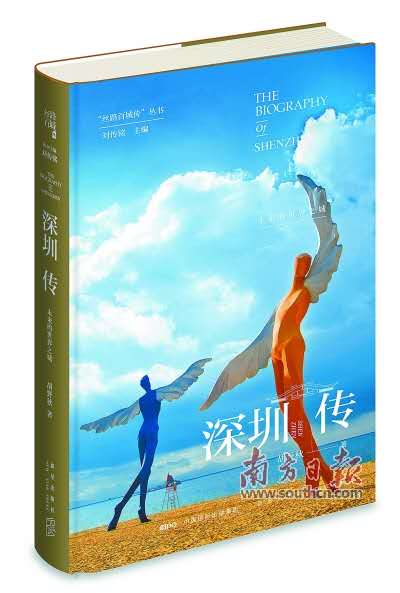
《深圳传》
胡野秋
新星出版社 2020年4月
●千夫长
胡野秋的新作《深圳传》,写出了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丰富多彩。作品视角丰富地进入深圳,纵向写历史讲民俗,横向言家国说人心,文本独特如《夜行船》,文字好看如黄仁宇,是一部多彩的深圳人文画卷。
胡野秋说,试图迅速而准确地描述深圳特区,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虽然它只有短短的四十岁,但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城市当中是非常突出的。
显然,胡野秋解决了这个困难,为深圳立传找到了多个支点。深圳不是日积月累建出来的,是用速度造出来的,甚至可以说是用梦想设计出来的。如此特别的城市,那就一定有特别的故事,而且,不仅仅是春天的故事。它的故事丰富多彩。
那么,作为这样一座城市的传记作者,个人的笔触和经历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胡野秋的身份曾经是新闻工作者,做过深圳特区报编辑、记者。胡野秋也是文化的,他作为深圳市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,为这座城市进行文化定位和价值导向,并编写出城市文化发展蓝皮书;然而,胡野秋的身份却一直与文学相关,曾经主持著名的对话活动《深圳晚八点》,对话六零年代作家群,出版了《作家曰》《六零派文学对话录》,为文学命名。其实,胡野秋在做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时候,就和麦天枢等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。看胡野秋的作品,报刊专栏的结集也都是极具文学性的,比如《胡腔野调》《冒犯》等等。
我作为深圳多个时期的见证者,荣幸地以作家身份,进入了胡野秋书写的这部传记里,现在就从我和作者与深圳的关系,来略谈几件小事。
当年做新闻编辑的胡野秋,在深圳特区报他主编的版面上,首开了我的第一个个人写作专栏《野鹤闲云》。那时,我的笔名是鹤野。后来,有论者认为这是国内最早开出的个人专栏之一。那时候,大概是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,我们在特区报和城建集团之间的蔡屋围、晶都酒店、红叶电影院、巴登街一带,上半夜在拥挤的大排档吃鸡煲喝啤酒谈文学,下半夜赤膊吹着风扇开始写稿。当时还没有电脑,全是手写的年代。第二天,上午一定交稿。记得,有一次我要出差去大连交易BB机,需要多天。就熬了一夜,连续手写了十一篇千字文给胡野秋提前交稿。
那时,我们都是留着长发,年龄也正是意气风发。在经济特区里,我们不经济但很文学,这也是我们后来都没成为老板的遗憾。现在,那些街店的名字都还存在,已经成了我们共同记忆里友情的刻度。
深圳是怎么来的?野秋在书里,经纬纵横,描摹得脉络清晰。我不赘言。那么,我来深圳干了什么?由于没有当成老板,我没有盖上高楼,也没有建造工厂,甚至公司都没开好,就是以作家的身份写了几本小说。一直以为,像我这样的特区闲人,没为深圳作出经济贡献应该愧疚。但是,当我的小说《长调》进入2007中国小说学会最佳长篇小说排行榜的时候,胡野秋在深圳商报上撰写文章说,我和那年青歌赛获得金奖的姚贝娜一样,是深圳的两个文化冠军。这一下子,我不但以我的小说为荣起来,还觉得也给深圳带来了一点荣誉感。一个城市最高的价值评估,应该是文化。
最近,在洛杉矶我把书稿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,也把在深圳多年的岁月仔细地回忆了一遍,真是愉快的悦读之旅。掩卷之后,深深地沉浸到怀想和惊叹之中。我和胡野秋是同年同月差一日的属虎狮子座的弟兄,我们最好的年华,是和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精彩时光一起度过的。因深圳这座城市的丰富多彩,显得我们的人生也丰富多彩了。
深圳之窗 微信公众号一大波便民功能上线啦!扫面下方二维码,关注后在微信对话框中回复“ 摇号 ” 即可实时获取申请最新结果;回复“ 电费 ” 即可在线查询用电信息以及缴费!

分享到


